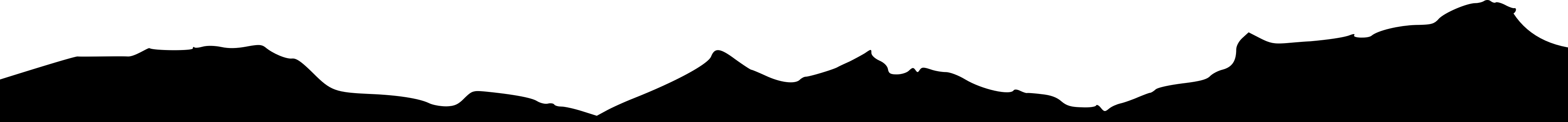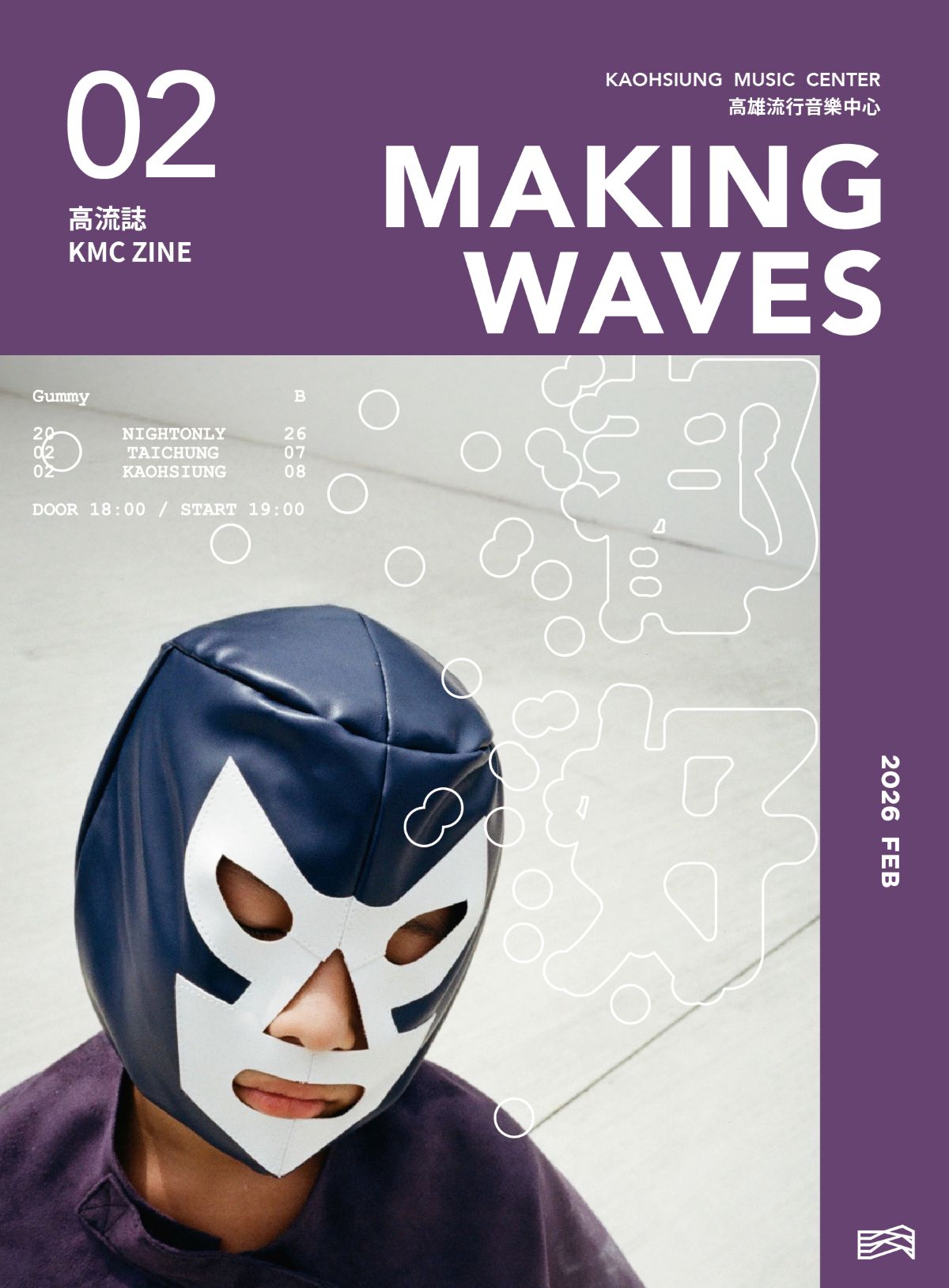拍謝少年,與我的心事——SORRY YOUTH「現場處理」@ LIVE WAREHOUSE
作者/寫作者・自由編輯 蕭詒徽 - 2025.09.04
演出中,當維尼和薑薑第 N 次帶著樂器走到舞台中央、面對面尬琴的時候,我忽然想起,上次回高雄時母親對我說,她漸漸聽不懂我說的話了。
像是回應我的回憶似的,薑薑在 talking 時提起了父親:「昨天是父親節,很多人應該都有回家陪爸爸媽媽吃飯吧?我也有。我就想到說⋯⋯因為我爸爸現在就是,我何時要表演、我在哪裡表演他全都知道,記得比我還清楚。但我考大學選科系時,他當時很希望我去考公務員。」
「出社會之後,我爸爸還是很希望我去考高普考,但我沒去考。當時只很確定自己喜歡玩樂團、而且有朋友一起玩樂團⋯⋯當時不怎麼支持我的爸爸,昨天跟我說:『你們這場不錯欸,三場都 sold out 捏!你們很有前途喔⋯⋯』」
台下聽眾歡呼起來。而我直到那一刻,才終於掉下淚。


因為話語,而非音樂而落淚,似乎有些不敬。但也確實,在音樂養成上以 J-Rock 為原點的我,浸淫在旋律線相對明顯、且樂於對和弦作繁複轉折的美學之中,似乎很難立刻成為拍謝少年曲風的愛好者。此外,由於過往的生命經驗,我經常在男性之間展示陽剛情誼的場合感到不自在。像團員在台上尬琴這樣的情景,理應是我會覺得無法進入的。
但每一次聽拍謝演唱會,我都感覺到無比舒適、安心。即使音樂喜好的光譜不同,我依然總能在他們的演出中被攜帶著、被動搖著。
拍謝少年二十週年了,也許是時候來想想為什麼。
簡約作為一種結盟
在這場二十週年巡迴《現場處理》拍謝少年專場中,演出間穿插數段歷年影像剪輯 VCR。有兩個畫面讓我再三回味:
一是宗翰在某場演出接過了一瓶烈酒,然後一口氣仰頭喝了大半瓶。
一是維尼入伍前讓朋友們剃他的頭髮。原本還笑鬧著,他卻突然低下頭來,哭了。
前者使我感到深刻的原因比較單純:六年前,我訪問拍謝少年,他們分享早期演出時與觀眾的關係比較有距離;轉捩點是 2015 年 Park Park Carnival。那場演出下大雨,團員請聽眾站近一點,這時有人從台下遞來一瓶威士忌:「我那天就像灌啤酒一樣灌掉那半瓶威士忌。」當年受訪時宗翰說,「從那次之後歌迷和我們的互動好像變得比較直接,要不然發第一張專輯的時候我們的場也沒人衝撞啊。」
在我心中,後者與前者的意義互為表裡,或許也是前者的一種佐證:樂團願意、並選擇團員情緒流露的片段放進 VCR 中,就像在說「再近一些」。而這兩個片段又都展示了一種常見、但有時會被忽略的陽剛形象:一種堅毅的、沉默的、略帶笨拙、不善言辭的陽剛形象。
性別研究史上,美國語言學家黛博拉.泰南(Deborah Tannen)曾提出「性別差異理論」,她視男女如同來自兩個不同的文化圈,彼此在語言的使用與身份的展演上各有傾向。尤其在語言上,男性常被認為偏向以語言交換資訊(「我等等要去哪」、「這可以怎麼做」);女性則更傾向用語言建立情感連結(「沒事的」、「拍拍」)。
泰南的理論被後來的性別展演理論所挑戰,展演理論強調性別是透過不斷的行動與表現被建構出來,而非既定的二元文化。但無論是以差異理論或展演理論來分析,拍謝少年選擇展示的「兄弟情誼」卻恰恰落在另一個軸線上:那些被放進 VCR 的片段,不是資訊交換的時刻,也不是用語言建構親密的瞬間,而是沉默的、甚至顯得不知如何表達的情感外溢。
這意外貼合這次巡迴的眉標「鐵漢柔情」。而正因為這樣的選擇/展演所建立出來的脈絡,當他們在台上一次又一次地尬琴時,我感受到的不是競技或較量的行動,而更像是一種默契的、在這個瞬間不以言語來交流些什麼、看看會發生什麼的行動。


這一點,也扣回拍謝少年在音樂上、甚至多數歌詞上的直白簡約——在創作策略上,比起展示天馬行空、無所不能的技藝,使聽眾仰望(這也是一種很棒、而且可能是我在美學上更習慣的聆賞體驗),拍謝少年的現場呈現了一種邀請聽眾平視他們、與他們共在的氣質。
不能完全精準掌控的自己,以及並不試圖展示全知的姿態。是在感受到這些坦誠的瞬間,台下的我們與台上的拍謝少年結盟了。
男性情誼負空間
或許因為回到他們視為主場的南方,演出中團員接連幾次放炮。第一次是維尼,但讓我留意的不是失誤本身,而是他在放炮後說的話:一定是因為演出前吃了兩顆肉圓的緣故。下一段 Talking,他甚至還補充自己吃的是他激推的莊家鹿港肉圓。
隨後,宗翰在另一段 Talking 裡提到今年蚵寮小搖滾將要復辦,還特地指認主辦人就在台下——熟悉拍謝少年的聽眾,對他們這種如數家珍的模樣並不陌生。不管是和作家黃崇凱的對談[1],還是和濁水溪公社的小柯一起做音樂時的閒聊[2] ,他們總能輕快地把某個地方的人情物事搬上檯面。那不是刻意的強調,而是一種隨口就能流露的親密。
在台上無意間展露出的、與地方的連結,對我來說又建立了一種獨特的男性情誼負空間。在藝術語境裡,負空間是指「主體以外、卻正是凸顯主體存在的部分」。負空間不是單純的留白,而是一種發生在主體之外的存在:它讓人有餘地去想像、去感受,甚至比具體的形體更具力量。拍謝少年與地方的關係正像如此——這些交流並不真正發生在舞台上,但在日常裡的互動、在各種訪談與分享場合裡,我們確知它存在,而這些關係成為了舞台上情誼展示的負空間。
他們並不只是來到一個地方,而是參與一個地方。正是這樣的負空間,支撐了演出與「此處」之間更進一步的共在,也讓他們的如數家珍顯得真誠而令人信服。是因為熟悉,才可以不多說什麼。
理論說得太多了。我想起小時候因為父親而長期收看的連續劇《親戚不計較》。兩位主角之一粗皮雄言行隨性、大而化之,是刻板印象中粗獷、不修邊幅的陽剛形象;另一位主角卓有春被地方稱作「紳士兄」,溫文儒雅,受人敬重,對外氣質收斂。兩人在劇中水火不容,亦敵亦友。如今回望,恰是不同陽剛氣質之間的纏鬥。
而這兩種看似相左的性格,被拍謝少年這個台語搖滾樂團在台前台後的行動,奇妙而成功地統合在一起。
靠山
就先不提〈暗流〉到底要不要拍手[3]的問題。拍謝的現場總是充滿大合唱。宗翰在台上笑著說,這系列演出的前兩場他一開始都講罷免的事情,因為罷免結果讓大家都蠻傷心的;但來到高雄就不用特別講了,因為這邊根本不需要投票。
我不禁想起726投票後,同溫層之間曾經有過的討論:取暖究竟是不是一種無用功?我想,拍謝少年那晚的演出再一次回答了,顯然不是的。雖然拍謝少年過去在訪談中提到,他們近年試著處理比個人更龐大的命題[4] ,但若攤開歌詞文本來看,他們的創作依然習慣用簡單的關鍵字去連結事件,再用直截的動詞去賦予情感動能(尋找、奔走、聆聽)。這種語言,更接近泰南所謂「較少傳遞資訊、較多建立情感連結」的特質。
曾經與拍謝團員聊過的人,都知道他們對各個領域的閱讀量都大;然而在創作上,他們並未選擇將學識上的厚度直接擺放於音樂中。這也讓我想起今年初,我和清大外語系、同時也是台大語言學博士的謝承諭老師交流,他提到語言學界在研究上古語時的一個發現:上古時期的詞彙量比現在少,概念也比較大塊、簡單,但正因如此,上古文本裡更常觸及哲學的上位概念,例如天、地、人生。這似乎揭示了一種狀態:簡約的語言,即使細節較少,卻同樣有機會——甚至可能更有機會——觸及深處,那些我們枝葉繁茂的心靈中的枝幹部分。
理解有時並不發生在說明,而發生在說明之外的層次。或許,那就是我們統一稱之為「默契」的東西。
也或許,就是被我們稱之為音樂的東西。


而是的,在高雄,對於某些事我們真的不用多說什麼。或許對拍謝少年而言也是如此吧?當他們的音樂長久以來成為某種可供依附的靠山時,某些地方也反過來成了他們的靠山。
在台下的我,有一種目睹靠山回到靠山的感覺。
現場處理
母親說她漸漸聽不懂我說的話了。我追問什麼意思,她解釋說,有時候我會用一些太難的詞彙,或者比較少用的詞彙。我心裡有些訝異——原來我的語言方式已經改變成母親無法理解的模樣。但為什麼呢?平常的我究竟在對誰說話?
那才是我真正落淚的原因。薑薑的父親在二十年後懂了他,而我的母親卻在二十年後不懂了我。
也許母親心裡期待的,也是那種簡單、直白的共在。而我在那一刻意識到,這不正是「現場處理」真正要處理的東西嗎?
示愛就是示弱。所以,有些時候,示弱就是示愛。
我的母親總是閱讀我的每一篇文章,包含這一篇。而我該對她說的,其實可能只是一句話:
「媽,我那天回家聽的是這個。」
拍謝少年二十週年《現場處理》演唱會
高雄 LIVE WAREHOUSE 歌單
02. 台十七
03. 契囝
04. 我們苦難的蘋果班
05. 噪音公寓
06. 佇驚惶中騎車
07. 共身軀完全放予去
08. 你愛咱的無仝款
09. 踅神夢
10. 夢中見
11. 我閣有偌濟時間
12. 上溫柔的所在
13. 時代看顧正義的人
14. 骨力走傱
15. 歹勢中年
16. 兄弟沒夢不應該
17. 深海的你or北海老英雄
18. 山盟
19. 暗流安可:無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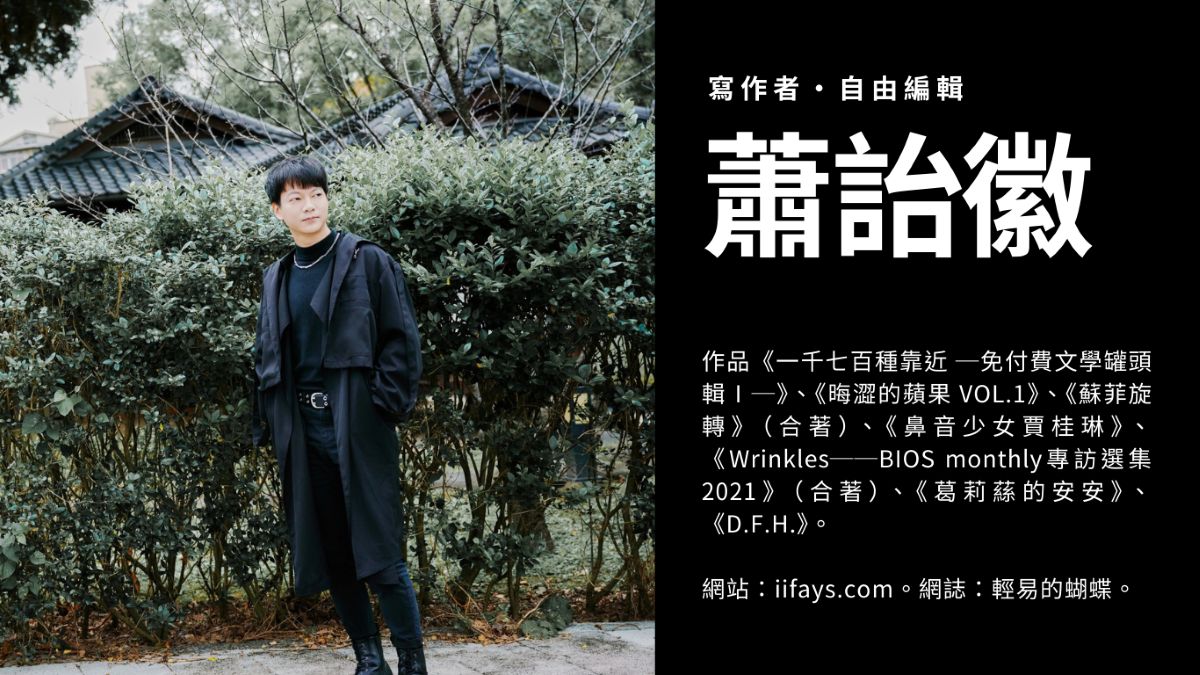
–
[1] 參考文章 《黃崇凱 VS. 拍謝少年(上):台派中年站出來!文學與搖滾樂的共時宇宙》
[2] 參考文章 《拍謝少年隨筆|錄音那天,小柯說他去操場跑了兩千公尺——《歹勢好勢》合作曲大揭祕》
[3] 參考文章 《〈暗流〉的前奏到底要不要拍手?關於召喚集體幻覺的的儀式》
[4] 參考文章 《黃崇凱 VS. 拍謝少年(下):乘著「新台風運動」 飛向有夢的未來》